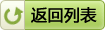|
回忆母校---我的南京大学
查看(1853) 回复(0) |
|
 小白杨 小白杨
|
发表于 2010-09-21 00:49
楼主
【最是那一耳朵的温柔】
回忆母校---我的南京大学 和菜头 我在1993年投考入南京大学,是埔口一期的学生。1997年,香港回归的七月,告别了母校。再过一个月,我就已经工作四年了。 在母校的四年里,一直在抱怨。抱怨伙食太差,抱怨宿舍条件太烂,抱怨校图书馆的书太少,抱怨漂亮的女生都被人先一步掐了。那时候,做梦都想尽快毕业,逃回我四季如春的家乡。毕业看似遥遥无期,但是我现在居然已经毕业四年了。听说大学同学里,生了孩子的都有了。真的到了社会上,虽然混得人模狗样的,夜夜笙歌,却总找不到大学时代的那种美好的感觉。现在的我,比当穷学生的时代日子好过多了,再不抽廉价的大桥香烟,再不喝简装的洋河大曲了。面对着金装红塔山2000,激光防伪的五粮液,却怎么也兴奋不起来,怎么也开心不起来。 我翻出毕业留言册,找出那些老照片,甚至寻到了印有北大楼的笔记本,看着它们,觉得伤心欲绝。这时我才发现,当年急欲逃走的我,其实早在心里埋下了怀念母校的伤痛。随着岁月的流逝,母校的魅力终于一点点显露出来,而我心头的伤痛也就一天天严重起来。我终于会发梦,梦见我又回到了南大,回到了北大楼下。梦醒的时候,那种思念的伤痛无比清晰,象是巨槌敲打着我的心房。 我很早就做了网虫。在网络上流浪的日子里,我最想见的就是来自母校的人。不为了什么,只是想问一问他们:紫金山的落日远了,玄武湖的荷花凋零了,鸡鸣寺的钟声沉寂了。你们在做什么呢?我的学弟学妹们?南园的林荫路是否依然?北大楼前的草坪上是否依旧人潮汹涌?情侣们是否还是相拥而过,甚至说着我们曾经说过的相同情话? 我在OICQ的聊天室里找寻,在网易的社区里搜寻,在5460的花名册上似梦似真,在小百合BBS上等网页展开到天明。我象离开了水的鱼,翕张着嘴,寻找润泽;象溺水的人,重出水面,如此贪婪的呼吸。我渴望听见哪怕一点点消息,一点点关于母校的消息。 我的母校没有北大和清华那样的显赫声名,甚至也没有一个显贵出自南园。她曾经是国立中央大学,这就是她的原罪。我永远无法忘记,那一年风雪交加的元旦之夜。先校长曲钦岳先生在校广播里致新年贺词和辞职声明:“国家对教育口惠而实不至,我已身心疲惫,万难继续校长的工作。”当时,国家教委承诺给予兴建埔口校区财政拨款,而最后却不见下文。母校在万难之下,毅然借款完工,却因此背上了数千万元的巨债。甚至有传闻说要卖掉南、北两园,筹措必要的资金。《南大报》全文登载了先校长曲钦岳先生的辞职文告,一片黯然。 就在这种变乱纷呈和筚路褴缕的时局下,我作为埔口一期的学生,开始了在埔园的学习。到今天为止,我都不喜欢埔口。记得当时我抵达南京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校车把我们送到江北去,看着一路上黑黢黢的景致,让人怀疑是否走错了方向。等到了埔口校区,两扇大黑铁门在车后缓慢而沉重的合上的一瞬间。我的心在“呯”的一声中,沉到了底。毫无疑问的,我觉得这里与其说是一个学校,倒不如说是一所少年犯管教所。而随后的半军事化管理,也证实了我的这种预感。 那时候的埔口,整个象一个巨大的工地。我们在校园里军训的时候,整夜都可以听见电锯的声音。甚至到正式上课了,走廊里还是堆放着很多建筑材料。最令人绝倒的事是一位仁兄,他老人家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在教学楼里急速奔跑,而他好象对玻璃门并无一点概念。。。。。。第二天我们去看事故现场的时候,只看见玻璃门上碎出一个人形,一地玻璃,还有明显的血迹。《南大报》专门就此写了评论文章,指责有关单位的疏忽大意。很快的,所有玻璃门上立即出现了彩色贴纸。 一种叫辅导员的奇特生物突然降临到我们中间,在习惯了十二年的班主任后,这些刚从学校毕业就直接由学生而曜升为管理者的人,给我们吃尽了苦头。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的脸上总不见一点笑容。而且,在其他系里,更流传着恐怖的故事,说辅导站怎么怎么厉害,如何如何变态。我们大气系和数学、哲学三个系组成了第三团总支,辅导员是著名的蒋恩铭同志。小蒋同志长着翘翘的睫毛和鼻子,一头卷发,看上去温柔无比。此公给我们的第一印象非常深刻,他是如此介绍自己的: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辅导员,我姓蒋,蒋介石的蒋,恩,周恩来的恩,铭,铭记的铭。他一口南方普通话,又快又急,我们一百多个人闻之大笑。过了几年,等我看了周星弛的《国产007》听见“飞是小李飞刀的飞,刀是小李飞刀的刀”时,终于明白,小蒋同志的先进之处。 相比其他辅导员,小蒋同志还算和善,不过也找过我的麻烦。那是98年的新年附近,校区里草木枯槁,北风呼啸,空气里还总带着扬子石化飘来的硫磺味道。面对如此萧瑟的景象,每个人都很想家。当时,全校只在每个宿舍下有一台电话,要通过校总机房来转。大约是机房人的心情问题,我家人打的几次电话都被封杀。当他们终于接通我并告知这情况后,我简直怒不可遏。当晚就写了一张大字报贴在一食堂前的报刊栏里,记得我说:“千里求学,苦于思乡。何至于荼毒若斯?”(那估计得算我的第一个帖子:-))我立即就被校奸出卖。小蒋同志找我谈话,问我究竟想搞什么搞?并且表示,已经保我不住,校区主任想和我谈谈,要我深刻反省。当时他一脸叹息遗憾,把我吓得屁滚尿流。后来,不过交了一份检查了事。小蒋同志在我离开南大的时候,已经荣升了。不知道现在是否真的“蒋介石的蒋”?先校长中,蒋中正可是其中一位啊! 既然开始了学习生活,重点自然转移到生活上去了。男生五舍和女生四舍是面对面的两栋,因此又了很多趣事。五舍的人在阳台上,就可以一览四舍的无边春色。不知道是哪一天开始,五舍里各个楼层都配置了大量望远镜。一到熄灯,一群光着梁子的兄弟就那手电往对面射。有时候,对面的女生用电筒或者是照相机回应过来,5舍顿时爆发出一片狼嚎。辅导员老师闻声出来指责,居然立即被上百把电筒照在脸上。欢呼声、掌声如雷鸣一般。这事的结果是:所有的电筒和望远镜都被没收了。还记得四舍四楼(408?)有一北京籍周姓女生,据说是南京大学埔口校区的金陵12叉之花魁(当时军训的时候,就已经评比出了金陵12叉,不是钗)。此人在夏日炎炎之时,常穿着极为暴露的衣服,在宿舍里打转。引得对面眼球暴出,鼻血狂喷,怪叫声连绵不绝。 埔口周围都是农田和鱼塘,我们就到埔口镇买来了鱼钩,把自行车辐条磨尖做成鱼叉,开始了我们的知青生涯。一般是在5点钟左右,钓鱼组的人就出发了。一是趁这时候守塘人睡得熟,二来这时候的温度不太高。他们曾经创造过一个记录,用一米五的竹杆,钓起了一斤的鱼。龙虾组在十点左右出发,由于中国农业部的失误,我们引进了一种美国产的螯虾。此种怪物性格凶残而贪婪,贪吃而愚蠢。只要有水的地方就能繁殖,而且在田埂上大打其洞,把水田变成了旱地,南京的农民恨死了这种蠢东西。一见我们,知道是去钓虾,他们立即热情的指路,把我们引到螯虾最多的地方。獒虾非常好吊,用肉皮或者小青蛙栓在绳上,放进水里。不多时你就看见水面有了动静,红色的大螯在水下挥舞,直接把绳子拉上来就成了。多的时候,一块肉皮上能有三四只呢。有的时候,它们也会松了大螯。逃回水里。但是由于它们是那么的愚蠢和贪婪,你在原来的地方重新放下饵,吊起来的往往还是它。正因为这样,一天的收成能有两大塑料桶。 龙虾组在钓虾的同时,青蛙组就去用鱼叉叉青蛙。一位来自吴县的钱英龙同学,可谓是个中高手。我们还什么都没看见的时候,他已经大喝一声“中”!鱼叉脱手而出,直飞前面某个地方,牢牢的钉在青蛙的后腿上。我从来都无法很好的使用鱼叉,只有一次,我叉中了一条水蛇,颇引以为豪。其他各组自行寻找吃的,在村子里有一片桑树,他们经常吃得嘴都紫了,才带回来一小捧桑葚。最搞笑的是,他们去地里偷莴苴回去凉拌,还美其名曰:借菜。呀日被一农人狂追,其中一个拖鞋都被追飞了。那农民追上他,看着惊魂未定的他,气喘嘘嘘的说:“同学,你们挖的这几棵太老了,不好吃,我带你去拿几颗嫩的。你别跑那么快啊!” 等回到宿舍,大厨当然是我。宿舍里不允许生火,但是管理员被我用一包烟搞定了。和菜头大厨创造性的发明了红烧龙虾肉,清炒小龙虾,青汤田鸡和糖醋鱼。一群男女生吃得大呼痛快,一直到后来的珍珠泉和紫霞湖烧烤,都是任命我为首席厨师长。在埔口的一年时间里,学习没有什么进步,但是我的厨艺却大大的上了一个台阶。那时候不知道为什么,老觉得饿。一群人简直如同是饿痨病患者,见什么都吃。从家里带来的油辣椒,开始的时候,南方的同学都表示不吃辣的。但是等到后来,他们下手比我都狠。甚至到今天,我在恶梦里都能看见他们天大地大的调羹向我飞来。 我的记忆里,埔口的生活真的非常象知青。但也有值得记忆的景色,在操场边,夏天夜里的时候。你能看见萤火虫。它们顺着上升气流,飘忽不定的飞上天去。那种美丽的萤光和流线,让我一直难忘,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在操场的另外一边,是我们的植树区,也是校卫队扫荡情侣的沙场。秋天的时候,长草过头,里面埋伏了很多情人。有人还起了个名字:情人谷。在情人谷外,靠近操场的地方,有一棵树,团团如盖。我曾经在炎热的夏日里到树下温书,那大概是我唯一一次在埔口温书的经历。 在94年春节前的一个晚上,大家的思乡之情达到了顶峰。我在12点左右,跑到阳台上。全校区一片漆黑,北风划过树梢,发出尖锐的啸声。我扯开喉咙唱张楚的《姐姐》。等唱道“姐姐,我要回家”一句时,几乎所有的男生宿舍里都传出一样的狼嚎般的歌声,到了最后,简直声震四野,我泪流满面,这是最值得记忆的事。 这就是我在埔口的岁月,埔口就是那么个地方,一个囚禁了无数青春和热血的田院。 埔口最后似乎成了我们所有人心头难以挥去的痛。我们最美好的青春,居然是在那样的高墙之后度过。埔口孤单单的站在长江的北岸,大铁门封锁了一切试图穿越的尝试。当最激昂的青春无从挥撒,热血被禁锢在四方的天空下,谁会对此心满意足,谁会在回忆中无动于衷呢?只是一道铁门,一道铁门,就残酷的把我们与梦想中的大学城分隔在世界的两端。 记得刚开学,在课间休息的时候,总听得头顶人声鼎沸。抬头望去,却发现教学楼顶上站满了人。甚至在休息的时候,依然有人会爬到行政楼和教学楼的天桥上。他们在干什么?他们在眺望。教学楼是唯一可以攀爬的地方,能看见远方的景色。向南,其实最多能看见泰山新村。长江上一年四季总是水气迷蔓,哪里可以见到南京城的景色呢?在记忆里爬楼是件有意思的事,现在回想起来,却觉得非常伤感。那时候,我们对新世界的向往,只能是登高望远,登高望远而已。 人在孤独中总会想抱成团,于是林林总总的同乡会在一夜之间出现了。海报亭里一到周末,所见的全是同乡会召集人马的招贴。我只参加过昆明和四川同乡会。因为我能操多种方言,其中四川话最为流利,所以经常随了本系的人冒充四川人,到处骗吃骗喝,顺便还可以看看漂亮的四川妹妹。妹妹最终没泡到,但是毕业的时候,居然分了我一份四川同学通讯录,菜头之变色龙可见一斑。其他的同乡会的情况我不是很清楚,参加最多的是昆明同乡会。说出来不怕大家笑话,同乡会最重要的一项内容居然是大家说昆明话。我因为能讲很多昆明话中最俚俗的土话而倍受欢迎。经常我讲出家乡一句土得掉渣的话,大家立即欢呼鼓掌,说是很正宗,好久没有听过了。在乡音里的乡愁,往往使这样的聚会持续很久。 同乡人大家沟通自然方便,但是一个系里的人却来自五湖四海,大家所操之国语简直洋相百出。记得我的上铺,是位来自湖北红安的兄弟。此人开始的时候,居然是用笔和我交流。他先问我:大消里消不消叟消?我听了二十几遍,一直怀疑此人对中国火药有深刻研究,满口的都是“硝”来“硝”去的,却不见下文有“木碳”、“硫磺”出现。遂用手势请他拿笔写字,他老人家一行仿宋体写下来,却是:大学里学不学数学?我当时就倒地气绝,拖鞋满天飞。另外一位仁兄是山西太原人,直到毕业都是一口太原腔,又含糊又冲,醋味充脑。上课的时候,他的名字还很帅,经常有年轻英文女老师请他起来念课文。他出口就是一篇打着滚翻着跟头的老醋英文,简直能把人笑死。教室里笑翻了天,大家捂着肚子就往课桌下钻。一开学,我们就欣赏了很多种英文:四川椒盐英语,东北菜帮子英语,陕西信天游英语。。。。。。据说北京英语---Beiglish不错,班里没有北京人,欣赏不到。但是想想“点头YES,摇头NO。来是抗母,去是够”,也好不到什么地方去。 大家一开始的时候,彼此之间都比较陌生,所以非常之客气。上个厕所遇见了,也必然打招呼曰:在上厕所呢?回答也特别谨慎:是啊,蹲着呢。后来熟悉了,也就乱开起玩笑来了。(女生不知道)大家一开始是首先交流各自家乡的脏话,躺在铺上,就互相询问:你们那地方骂人最狠的一句是什么来着?然后做念念有词状,其刻苦程度,便是文王转世也望而兴叹。后来博取百家之长,荟萃各地之精华,大气系提出了男生标准骂法:“你个呆皮!我阉你就象阉只蚂蚁一样!”其语言之毒,骂人之狠,设计之精妙绝伦,到今天我都感慨不已。谁说人民群众不是最有创造性的呢?再后来,每人每句都带大学男生标准口头禅“哇操”,根据我的统计,最高频率出现在宿舍聊天中,平均每一句话里带三个。类似:“哇操!今天的饭,哇操,简直和哇操子弹一样!”有的还喜欢在每句话最后,意犹未尽的补上一个。毕业以后,上了一天班,我居然彻底忘记了这种语法结构。真是奇事一件!特别记之。 埔口的岁月里,总是让人感觉到饥饿。我时时背诵鲁智深的名言:“这几日,口里淡出鸟来。”开学时形成的原始共产主义迅速土崩瓦解,有人开始在半夜十二点偷偷拿饼干出来在被子里偷偷的啃,几乎被革命群众当成老鼠打死。那时的埔口,只有两个小卖部,教学楼里的一放学就关了,食堂门口的也在饭后飞快的关门。你想在晚上买点什么东西吃,根本不可能。埔口吃饭的时间特别的早,大约五点半开始,不到六点就结束了。当时最可恨的就是校广播室的,一到吃饭时间就放张学友的《吻别》、《每天爱你多一些》等歌曲。毕业以后,一听见张天王的歌,还没等欣赏,肚子就条件反射一般叫起来。张学友估计做梦也想不到,他的歌曲居然会成为了巴普洛夫的那个铃铛,在埔口。 宿舍下面开始卖方便面了,北京牌的,五毛五一包,同时也卖火腿肠,全面粉的。其他的,还有北京牌方便面和面粉火腿肠。你完全有自由选择吃或者不吃。我有生以来吃过的最难吃的方便面就是在埔口吃的,到了南园的后,我曾经在青岛路的批发市场和北京牌方便面邂逅,当时的心情很复杂。就象是在五十年后遇见小学那个暗恋的女生,她已经是个臃肿的老太太,因此怀疑自己当年是怎么了?即使是这样,你的面条还不能保证完好无损的吃下去。日子艰难,校区的共产风越刮越厉害。尤其是那些人缘好楼层高的人,从一楼煮了面出来,层层楼梯都有人把守,雁过拔毛,还美其名曰:“只喝一口汤。”言辞间大有小兵张嘎》里胖翻译官的“吃你两个烂西瓜!”的气概。大气系在五楼,有的人到五楼的时候,只有两种选择。选择A:喝下最后一口汤,哭着睡觉去。选择B:下楼再煮一碗。 因此,那时候非常流行过生日。其实就是借口大吃一顿。埔口里就两个饭馆,当时属于严重垄断行业,我那时太年轻,换了今天,我一定在网上骂得某些人祖坟冒烟。其中一个位于校门口的山头上,其特点是:豢养了一万多只苍蝇,我当时估计是宠物。你冒冒失失的推开门,没有和它们打个招呼,它们能立即把你推出来。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风味食堂,虽然你可能忘记了它的名字,但是你的胃总能记得的。由于该食堂上菜是以半小时一个而闻名的,所以,你要是在这里召开生日晚宴,就得小心。往往是酒比菜下得快,菜还是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酒已经喝得太高了。从风味食堂里出来的人,没有迎风不吐的。你受尽蹂躏的胃一定对它印象深刻。如果还有另外一个人记得的话,那就应该是你的钱包。半小时一个菜,吃饭的人都等成狼了。见什么吃什么,一个菜上来,不到五秒,就已经瓜分一空。在风味食堂最后吃下来,每个人能吃出平常几倍的菜来。有次,校区停电,在突如其来的黑暗里,我就看见一圈绿光闪闪的眼睛,女生的还有红光在里面,非常好辨认。 在风味食堂,我大醉过一次。我记得很清楚,那是1997年11月3日,星期一,晴。下午体育课,我们逃到操场边的水田里抓龙虾。那时候还根本不知道去钓,看着田埂上有洞,就伸手下去摸。天可怜见,那其实是用我的肉身去试探龙虾的真身。龙虾一见我的肉手下来了,哪里还客气,立即就夹上了。然后我一声怪叫,顺势把手抽出来。如是者三十余次,可怜我一双猪人玉手,被夹得血肉模糊。同学们为了安慰我,决定当晚为我在风味食堂过生日,并且邀请了我暗恋女生来,以壮行色。该女生对我的兔子(生于1975年)野心早就洞若观火,准备对阶级色狼的野心给予毁灭性的打击。在桌上,她冷冷的望着我,把满腔的压迫苦阶级恨,都通过她的一双明眸表现得淋漓尽致。我当时手又疼,风又冷,菜不见上,过生日却不见个笑脸,却似乎是鸿门宴。于是空腹喝酒,一瓶52度的洋河喝完了,又上一瓶36度的。不到半小时,我就疯了。觉得心里郁闷难当,想去跑步。连美国阿甘跑步,其实都在我之后。大家拦都拦不住,我象疯了一样,跑到操场上。最后,还是被革命群众打昏了拖将回来。第二天统计,共失去眼镜一副,皮鞋一只,护身符一个。从此,失去了妈妈给的护身符,我四年里彻底走上了一个酒徒的道路。 1994年的夏天,南京的温度达到了42度。在五楼的宿舍里,一过11点,就没有电也没有水。赤身露体的躺在草席上,却辗转反侧,怎么也无法入睡。每个人几乎都以学习英语的名义,买了收音机。在炎热的夏夜里,我们彻夜开着收音机,等待着《零点有约》节目,等待着一个叫李婵的女人。“在如此寂寞的夜里,你睡了吗?朋友?还是守在收音机前?让李婵陪伴你度过这一段美好的时光吧!”李婵甜美的声音不知道构成了多少男生的春梦?我总觉得她那种媚到骨头的声音,和二战时的东京玫瑰可有一比。而我们就象一群美国大兵,在营房里艰难的等待着凌晨四点才会起的凉风。 李婵的节目在四年大学生涯里一直陪伴着我,在我最悲伤的时候,最痛苦的时候,只要打开收音机,听上一段她的话,我就会开心的要死。因为她的节目经常出现这样的经典句子:“。。。刚才,和大家说了那么多。其实,李婵也不知道和大家说了些什么?”间或有热心听众打进电话去:“喂喂喂?是我妈(吗)?是我妈(吗)?喂,李婵哎,你不晓得我有剁(多)高兴!喂,你啊晓得,我震(真)的很喜欢泥(你)的哎。”如此妙主持和妙听众,经常让人听的越来越兴奋,一直笑到三点。 在记忆中,那一年真是热。我就象一只阉鸡一样,打不起半点精神。一个星期的时间里,我只到食堂吃过三次饭,其他的时间都是吃西瓜。校园里的田鼠都举行了游行示威:埔口的呆胡!我们已经啃不动你们的西瓜皮了!!!以我那么生龙活虎的人,面对着穿那么少的女生,我居然没有一点点多看一眼的冲动。只想低头赶快回到宿舍,把衣服脱光了,冲一个凉,可想见当时的炎热。六月的一天里,我创记录的冲了十次澡。在小小的冲凉房里,身子外面是水,肚子里也是一包水。 天气如此之不堪,但是试要照考。现在过去四年了,我也可以坦诚的向大家交代了:我根本不会高等数学。教我们数学的是张明生博士,此人一般只上半堂课,然后诚恳的对大家说,同学们,一定要出国去!就出国这一话题发挥半堂课。我本身数学就很烂,加上只听后半堂课,所以到考试的时候,你们应该了解我的痛苦。教室里温度比外面还高,我心里由于焦急,温度更高。当时真的是挥汗如雨,翻卷子的时候,根本不需要用指头。拿满是汗的手臂往试卷上一沾,就OK了。到今天回忆起来,我都不知道我在卷纸上回答了点什么?只记得上面全是汗水和盐。 校方最后提前放假,叫大家回家避暑,下学期回来再继续考试。因为天气热而停止考试,我有生以来只遇过那么一次。正好,我趁机溜到女朋友家去了。 和炎热的夏天想对应的,是南京寒冷的冬天。南京的秋天几乎是在瞬间就到了,草木在一夜之间就可以变成了黄色。我们曾经去了一次玄武湖,说是游玩。当我踩在厚厚的落叶上时,目睹如此萧瑟的景致,我当时只想哭。从南方来的同学最不能适应的就是这样的四季分明,南方的秋天哪里有南京那样的萧瑟,充满了杀伐之气。中国古人认为秋天属金,主杀伐,所以就秋后问斩的一说。经历了南京的秋天,你才会感觉到,为什么秋天主杀伐。埔口周围丘陵上的树都落叶了,只剩下光秃秃的树干。树下的长草也都枯黄了,秋风一起,看它们在风中摇曳,象是在唱着挽歌。在小小的校区里,环顾四周,你会感觉到你的心也在凋零。 冬天终于到了,等你早晨起床发现窗子上有冷凝的水气时,冬天就真的到来了。北风吹过空旷的校园,被电线和屋角所撕裂,发出凄惨的尖啸声。你裹着被子,缩成一小团,桌上的台灯由于华东电网的不稳定,一明一暗,觉得简直是在世界末日。这种心理上的摧残还能忍受,因为春假很快就要到来。而生理上的痛苦,就更令人难以忍受了。在埔口的冬天里洗衣服,那种滋味真让人难以忘怀。水的温度太低,几乎无法融化洗衣粉。你用一个手指搅拌一下,那种寒冷的能立即穿到你的脚跟。你用一万个理由说服自己,鼓起勇气,一声惨叫,把手放进水里,马上你的第一反应就是用牙齿吸冷气。你站好马步,强行运起内力,将真气灌注于两手之上,象个烈士一样揉起了衣服。 南京本地产的洗衣粉的威力开始发挥出来,你感觉到很小的颗粒在你的手掌间磨擦。不多时,你的感觉就麻木了。寒气在这时候开始渗进你的骨头,你感觉到的是剧烈的疼痛,从骨髓里的那种痛。你忍受不了了,把手从水里缩回来。你发现自己的皮肤已经变成了奇异的红色,但是就在那一瞬间,你又会把手放回水里。因为皮肤上有水,风吹过的时候,感觉象是小刀在割。在这种反复中,你艰难的洗完了衣服。手指已经麻木,脸已经扭曲,眼睛已经充血。你只想狂叫一声:“不要!我什么都招了!”你用毛巾擦干了手,这时候你的手象发了高烧一样,让你感觉到灼热,用脸贴上去的时候,却依旧冰凉。许久,你的手终于恢复了过来,但是另外一种火辣辣的疼痛又吸引了你注意力。那种洗衣粉已经在你的手上偷偷开了无数小口子,象是无数的针刺。 每个人都在第一年里盼望着春节的到来,盼望着回家。思乡的感情在每一个空气分子里蔓延。夜深了,宿舍里的人却没有睡。话题一般由“老张,春节你家吃什么”开始。中文再烂的那个人都能在床上口述一篇优美的回忆散文,平常口吃得无法沟通的人,也能在那时间用类似赵忠祥般浑厚而充满深情的声音把浓郁的思乡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每个人都在说,听的人似听非听,其实早已经神驰天外,回到他万金不换的草窝里去了。话题似乎永无休止,说完了吃的东西,又谈各地的风俗。谈完了奇风异俗,大家又开始回忆自己的家是什么样子的,门在哪里,厨房和客厅的位置,在什么地方会有零食,什么地方放了一本写真集。在那些夜晚里,家似乎成了天堂,家里的什么东西都显得那么美好。我甚至清晰的记得,我当时刻骨铭心的怀念我家放在门背后的那把条帚。我甚至打算,等火车到达昆明站的时候,我会跪下来,亲吻昆明的土地。回到家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去看望我的老条帚,希望这半年时间里,它过得好。 第一学期的期末,思乡是一种狂热,是一种流行感冒。甚至你和什么人要动手了,你突然问他一句:今年春节你回家吗?那厮也会立即放下捏紧的拳头,眼波里全是温柔的波浪,嘴笑浮现出动人的微笑。甚至是江苏省的同学,他们的思乡之情也于我们这些远离家乡万水千山的人一样。周末的时候,教学楼里几个IC电话都排满了人,等待着给家里打一个电话。严冬的到来,艰难的环境,让人更加的渴望回家。那一年冬天里,最流行的一首歌是张楚的〈姐姐〉。我分不请什么是姐姐,什么是家。我也希望着在千山之外,在寒冷萧瑟的南京,又一双温暖的手,牵着我,带我回家。回到那一千条河流,一万重远山之外的故乡。那里是温暖如春的,不再有寒冷和孤独。那里是安全的,我可以在睡了十年的床上一下进入梦乡。因为,关了灯的家里,非常安静,我的泰笛熊在台灯边看护着我。 我再也没有坐过比第一学期回家时更慢的火车了。家乡据说会在某一个时刻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但是时钟总是如此的慢,似乎被什么粘住了。火车外的景色再没有的十月份出来时那么吸引人,我在焦急不安中催促火车再快些。我甚至不和人交谈,因为根本没有情绪去说话。等到火车转入云南境内,那象是被血染红的熟悉的土地终于出现在我面前时,我的泪水滚滚而下。高原的罡风吹拂着我的头发,空气里又是亲切的味道,雨后泥土的味道,家乡的味道。 1994年的春节前,我们回家了。 附记:血仍未冷 我都没有想到,我的一篇小东西,得到了那么多人的喜欢,在海外的同学居然都能看见。我想,埔口的岁月有很多苦难,但是我们走过来了。就象一位每个星期天从南园回埔口看女朋友的人,已经和他所爱的人在温哥华的阳光下享受着生活了。回忆过去,所有的苦难都变成了甜蜜。在记忆中结出沉甸甸的金果。 埔口岁月是我们自己的,而我们的感受绝对不会是校刊上我们整齐的军训队伍,不会是迷你图书馆馆里做刻苦学习状的学子。在埔口一年,或者两年的时光,给予我们的感受太多太多。我们来过,爱过,哭过,笑过。若如此简单的把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故事,我们的悲欢,简单的封进官方文件,一任上面落上灰尘,我到死都不会甘心。我们存在过,就必须留下我们的足迹。 我相信,在浩瀚的比特之海里,我们的故事将以这样或者那样的形式流传下去。作为文本也好,作为记录也好,我想通过我的笔,趁着我还年轻,血还没有冷,把这些感受和故事写下来。让后来的人可以看见,在南京大学的历史上,曾经有多这么一群人,曾经这么生活过,爱过,唱过,走过。 尤其是对于我在外地和海外的同学们,我们也许终生不能再见了。只是在南京大学的四年里,我们在时空上的这一点上相聚,随后就象飞矢一样,一去不回。一想到,我们会在以后几十年里同样生存在这世界上,彼此清楚的知道这一点,却无法相见,这种隔离的感觉真让人窒息。但是,我能让你们看见我们的故事,做到这一点,我就非常满意了。 我们分散在各个时区,当我写做时,也许你正在入眠。但是,请你们相信一点,我思念你们。请让我听听你们的声音。我想你们!晚安 |
|
回复话题 |
||
 上传/修改头像 上传/修改头像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