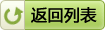|
传播学在中国20年
查看(1025) 回复(0) |
|
 tingyu tingyu
|
发表于 2010-10-01 11:50
楼主
[内容提要] 本文论述了传播学在中国20年的发展轨迹以及在这轨迹上的几个亮点,并对传播学未来走向进行了预测。
[关键词]传播学 发展轨迹 亮点 未来走向 传播现象在中国古已有之,而正式作为一门学问的“传播学”(The Science of Communication),则完全是从国外引起的“舶来品”,其最早的引起可以追溯到50年代①,但当时的影响极为有限。如果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初具规模的译介算起,传播学在中国也只有区区20年的历史。 但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20年。这是中国思想解放、经济转轨的20年。正是在这样的年代背景之下,传播学在中国获得了生长的土壤和空间,完成了从起步到腾飞的发展阶段。 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轨迹 放眼看世界——引进与起步 关于传播学在中国大陆的引入问题,一般可分为两次。一次是50年代的早期引入,这方面的代表人物当属郑北渭、张隆栋、王中等教授,他们在教学及研究中都曾有过运用传播学相关知识的先例,复旦新闻系的一个没有刊号的杂志《世界新闻译丛》也曾比较系统地介绍了传播学②。可惜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这种引鉴刚刚露头便无疾而终,很快就中断了。再次的引入已是20多年以后的事情。70年代末,复旦大学新闻系创办的一本内部刊物《外国新闻事业资料》上介绍了传播学的一些情况;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写的《传播学(简介)》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以此为开端,一批西方传播学著作也相继在大陆出版发行,如《报刊的四种理论》(1980年)、《传播学概论》(1984年)、《传播学的起源、研究与应用》(1985年)、《传播概论:传媒、信息与人》(1985年)等。后来许多学者将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这一举措视作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的真正起步。 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在这一时期,百废待兴的中国开始敞开胸怀,放眼看世界。改革开放,是传播学在中国呱呱坠地的催生剂、助产士。 投身改革潮——纸上谈兵与介入实际 传播学这个新生儿、外来户要想在中国的土地上扎根、成长,惟一的选择就是融入实践。在经过引进和起步阶段之后,传播学开始了对中国传媒实践的关注,为新时期中国新闻改革提供了理论支持。 首先是对传统新闻观念的冲击,新闻机构开始被称为“新闻媒介”、“传播媒介”、“大众传播媒介”,从而回归并突出了媒介本身的特点。“信息”、“反馈”、“把关人”、“受众”、“传播者”、“传播渠道”、“传播效果”、“意见领袖”、“双向传播”等一系列概念的引入,给新闻学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以至今天的“新闻学”已逐渐被“新闻传播学”所取代;其次是对于媒介功能的重新认识,即从“阶级斗争的工具”转向“传播信息的工具”,强调信息传播是媒介的基本功能,其他功能的实现都必须以此为前提;第三是促使实现由传者本位向受者本位的艰难转变,而这是与传播学的核心理论——受众理论的影响直接相关的;第四是对效果理论的研究,促使实务界重视与传播效果有关的各个因素,如不同媒介个性特点的研究、对信息本身的研究,受众调查成为媒介改革的重要举措和依据。所有这些,都对新时期的新闻改革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影响,余波至今未息。 洋为中用——中国化与本土化 如果说80年代初传播学的引入在中国新闻界起到振聋发聩的冲击作用,直接为新时期的新闻改革提供了理论支持的话,那么与此并行的研究也开始更多地向纵深发展,更多地关注传播学的中国化、本土化问题。1982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上提出的“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新”的16字方针,对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具有战略性指导意义;而1986年召开的第二次研讨会更是明确提出了“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的目标,此后传播学者本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态度,运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西方传播学理论进行初步的汇集、梳理、分析、运用。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有:居延安的《信息·沟通·传播》(1986年),邵培仁、戴元光、龚炜的《传播学原理与应用》(1988年),周晓明的《人类交流与传播》(1990年),徐耀魁的《大众传播学》(1990年),张隆栋的《大众传播学总论》(1993年),李彬的《传播学引论》(1993年),张国良的《现代大众传播学》(1995年),胡正荣的《传播学总论》(1997年)等等。与此同时,传播学者还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和传播实际出发,开展大规模的大众传播效果调查、受众调查、民意调查以及一系列专题调查,如陈崇山、弥秀玲的《中国传播效果透视》(1986年),赵水福的《中国社会心理的轨迹:亚运会宣传效果调查报告集》(1991年),柯惠新、张帆的《亚运宣传效果调查》(1991年),喻国明有关报纸读者的调查分析(1995年),丁俊杰、黄升民主持的中国城市消费调查(1996年至今)等等,传媒常有报道,影响较为广泛。 尽管如此,20年来中国传播学者研究的主流还是引进和介绍西方传播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说,传播学的中国化、本土化还远未达到成熟的地步,在为我所用、自主创新方面做得不够,与传播实践之间也存在距离,尤其缺乏一种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即便上面提到的书籍和教材,也多是以“概论”形式出版的,专门研究传播学中某一重要传播理论或专论传播模式、传播研究方法的学术专著至今尚未出现。值得注意的是,传播学界已经开始了富有探索性的尝试,出现了有一定特色和影响的作品。如沙莲香主编的《传播学》(1990年),大陆、台湾、香港三地学者合作、孙旭培主编的《华夏传播论》(1997年)等。前者设立一个章节专门论述“中国的传统传播方式及其特点”,后者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播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和探索。作者在借鉴西方传播学理论体系和研究模式的同时,致力于研究中国的传播历史和现状,并将它融入中国的大众传播实践,更多地以中国文化传统作为背景和参照,以中国国情为坐标,显示了中国传播学者的开拓勇气和创新精神。 世纪主题——趋向多元与精致 世纪之交的中国传播学,在经历了引进和起步阶段之后,日渐呈现出起飞的态势。表现在学术研究上,就是分支方向的多元化和研究内容的日益深化。作为一门多级交叉学科,传播学不仅涉及新闻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还涉及语言学、人类学、哲学及相关的技术学科,是在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交合点上形成并发展起来的综合科学。 这一“边界不清”、“多元共生”的学科特点决定了其发展的基本走向,也是它在现代及未来社会日益受到学界重视的重要原因。正在研究中的传播学涵盖内容十分丰富、涉及边缘相当发达,如“大众传播与市场经济”、“大众传播与大众文化”、“科技进步与传播发展”等相关课题日益成为中国传播学者关注的热点。 传播学学科本身的多元化也导致其研究方法的多元化。除运用对传播学发展影响最大的定量研究方法之外,文化学、后现代哲学、文本分析、意识形态分析以及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都开始运用,从不同层面和角度推动了传播学研究的拓展和深化,也使得传播学研究更加科学化、精确化。但就目前情况而言,能够熟练运用现代研究方法或就方法本身进行研究者尚不多见,经验研究与实证分析的力度和系统化也还有待加强。 传播学发展轨迹上的几个亮点 当我们勾勒传播学在中国的基本态势,描绘其发展轨迹时,有几个亮点不容忽视: 寥若晨星的零散译介传播学之所以能在中国传播开来,除了社会历史的大背景外,早期为数不多的译作为我们的研究和著书立说提供了直接的思想及资料来源,功不可没。 1978年7月,复旦大学新闻系创办的内部刊物《外国新闻事业资料》发表了郑北渭教授撰写的《公共传播学的研究》和《美国资产阶级新闻学:公众传播学》,虽然只是登在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上的两篇介绍性文章,却如同一石击水,在当时一片平静的国内新闻界掀起波澜。在此后的整个80年代,传播学在中国大陆基本上是属于学习和应用阶段。除由中国大陆学者自己撰写的第一本评介传播学的著作《传播学》(简介)(人民日报出版社,1983年)外,较有代表性的译作包括:[美]威尔伯·施拉姆:《报刊的四种理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译,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美]沃尔特·李普曼:《舆论学》(林珊译,1984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内部资料,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美]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传播学概论》(陈亮、周立方、李启译,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美]沃纳丁·赛弗林、小詹姆斯·坦卡特:《传播学的起源、研究与应用》(陈韵昭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英]丹尼斯·麦奎尔、[瑞典]斯文·温德尔:《大众传播模式论》(祝建华、武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美]梅尔文·德弗勒等:《大众传播通论》(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日)竹内郁郎主编:《大众传播社会学》(张国良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为数不多的译本如同点点星光,照亮了大陆传播学寂寥的夜空。 日益规范的各届研讨会 回顾传播学在中国走过的道路,不能不提起几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全国性的传播学研讨会从1982年的第一次算起,至今已经成功举行了6届。这6次研讨会每次都有可圈可点之处,并且在规模、规范等方面渐次扩展、完善: 1982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参加者只有二十几人,除黄可凤、张黎等人翻译的几篇文章外,没有其他论文。但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学者们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对后来的传播学研究产生重大影响的16字方针,从而确定了中国传播学发展的基本方向。会议还将开展传播学教育、研究提到议事日程,对后来一系列相关工作的开展起到了动员和组织作用。 1986年在黄山召开的全国第二次传播学研讨会上,已有学者提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 1993年在厦门大学召开的第三次会议上,则出现了一批与中国传媒实践结合起来的课题; 1995年在成都召开的第四次研讨会开始关注传播学的学术定位,着重讨论传播学的本土化问题; 1997年在杭州召开的第五次研讨会上,大陆、台湾、香港的传播学者首次欢聚一堂、共同探讨; 1999年在上海复旦大学举行的第六次传播学年会,首次尝试采用与国际接轨的较规范的国际会议的操作方式,规模、议题、质量等方面都有了相当的拓展,成为世纪之交名副其实的传播学盛会。 影响深远的受众调查 要论传播学对中国新闻传播实践的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受众调查的兴起。早在1979年,复旦大学七七级一批敏锐的学生,就曾用刚刚习得的传播学方法,尝试在传播学的理论框架下开展调查,进行现在传播学很时兴的“受众研究”,当时正赶上林彪江青集团受审。他们抓住这一重大新闻,及时调查受众是通过什么渠道知道这一消息的。尽管调查规模很小,但因其时间较早而产生了一定影响。 大规模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调查当属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和首都新闻学会调查组共同发起的北京地区读者、观众、听众调查,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受众调查。 这次调查从组织机构的权威性、规模、统计规范程度等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调查结果发表后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国外传播学者认为“中国传播学研究者在进行研究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③。国内新闻界则认为“北京调查”是“我国新闻史上一次突破性的行动” ④,我国新闻学实证研究由此开始,受众观念、受众理论得以建立并强化,受众研究组织相继问世。对中国受众的研究,是探求中国人的传播活动规律、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的关键所在;受众研究还培养和锻炼了一大批专业调查人员,带动了整个社会各行各业的调查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说,北京调查对中国的大众传播实践乃至中国社会的发展影响深远。 不断擢升的学科地位 传播学在中国的引进更多的是走民间道路。即便如此,由于受人们头脑中多年形成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定势影响,传播学的引进和发展充满了曲折。无论在四十多年前还是十几年前,传播学都曾被当作“资产阶级新闻学”加以批判性介绍。1983年传播学被批成“精神污染”,有些老教授认为传播学的要害就是否定阶级斗争;1989年又有人撰文批判传播学不讲阶级和阶级斗争。直到1992年的再次思想解放,才彻底改变了传播学在中国的历史命运。 早在1995年的国务院学科目录上就把新闻学和传播学并列为一个专门的二级学科;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式将传播学列入博士、硕士专业目录,新闻与传播学成为国家一级学科,这种学科地位的升格是传播学作为一门学问、一种学科正式被国家和社会所承认的重要标志。有学者认为这对推动传播学在中国的建设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同时也说明高层领导具有符合时代潮流和世界潮流的战略眼光,因为21世纪是信息唱主角的时代,如果一个国家的政策和学术研究不关注这个基本的核心问题,那么这个国家的学术思想就很难称得上先进。 对传播学未来走向的预测 “框架说”与“交融说” 站在新世纪的地平线上,传播学者对未来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走向寄予很大关注。关于传播学的学科建设问题,目前有两种预测,即所谓“框架说”和“交融说”。 持“框架说”者认为,新世纪传播学的首要任务在于积极构建自身的理论体系。传播学虽然具有“泛化”的特点,但它并不是各学科知识的简单拼凑,而是有着自身规律的、由一系列传播学的基本概念、范畴、判断、原理构成的具有严密逻辑性的知识体系。西方传播学发展至今,形成了形形色色有关传播模式的理论和观点,但所有理论最终关注 的焦点仍是传播学理论体系的构建问题。对于中国传播学来说,在经历了引进和起步阶段之后,腾飞的关键就在于建立自己的学科体系和理论框架。 对于传播学的未来发展,笔者更倾向于“交融说”,即除了继续研究高度抽象的普遍传播规律之外,传播学根本的生命力还在于和其他学科的交融共生,也就是说未来发展的空间除继续关注大众传播外,更多地在于建立和发展自己的分支学科,如跨国传播、组织传播、人际传播、文化传播以及管理方面的传播等等,这方面的发展前景十分看好。这种将研究分解到各个专业领域中去的趋势,将促使传播学更多地贴近生活、在理论与实际的多个层面上加强与社会现实的互动,进而使立足于中国传播实践基础上的研究大量增加。 传播学本身是一个交融、边缘性的学科,需要多学科的人来共同建设。传播学与其他学科的交融已越来越多地影响到传播学研究及教育领域。一些综合性大学也开始关注传播学,在一些专业性院校开设研究方向、专业乃至创建整个系。值得注意的是,各学校都根据自身的学科优势进行相关研究和教学,如北京广播学院依靠电子媒介的优势,主要发展广播电视教学与研究,又开始关注网络传播;清华大学、上海大学等则更多地抓新媒体,以求在传播技术与艺术的结合点上多做文章;北大、复旦、人大可能会更多地结合平面媒介,同时发挥其人文学科基础雄厚的综合优势;有些经济院校则会更多地与经济、企业管理结合,研究营销沟通广告等;还有一些师范类院校就更多地搞教育传播、艺术传播等。总之,未来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会更多地与每个学校的学科优势相结合。 引进与创新并举 传播学在中国20年的发展轨迹固然不乏闪光之处,但总的来说还是处于学习和应用阶段,真正的创造很少。创造的前提是学习,“我们积累得越深厚,研究思路就越明晰,就越具有超越他者与创新的可能,也就越拥有总结与提出新的传播思想及理论的能力” ⑤。只有对西方传播思想及其理论观点产生的背景进行广泛而有深度的探讨,才能为中国自己的传播学学术建设提供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参考框架,同时也建立一个真正的学术交流的对话平台。随着研究的深入,许多学者认识到,我们对国外传播学经典名著及新进展的介绍还很不够、很不完整。与台湾相比,后者就有好几套传播学译丛,仅“远流”一家出版社就出版了四十几种,而大陆整个加起来也不过一、二十本。较具规模的是最近北京广播学院与华夏出版社合作,“首选那些经过教学与实践严格检验,在西方传播学界有较高声望和影响的优秀教材和经典专著” ⑥,出版“高校传播学经典教材译丛”,仅第一辑就有12本,面世后引起较大反响。在西方传播学发展迅速、成果不断的背景之下,引进与创新并举将成为中国未来传播学的主流。 两岸三地交流日盛 由于历史的原因,港澳台等地区传播学的发展与大陆相比,在阶段上有一定差异。从70年代开始,一批留学欧美的台湾、香港学者以更大规模、更严格的规范较系统地引介了传播学及其研究方法,并开始了独立的研究。此后,其研究水平总体上领先于大陆地区。 台湾传播学研究萌芽于60年代初期,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为首批留美归来的传播学者,如朱谦、漆敬尧、徐佳士等。70年代堪称台湾传播学研究的起飞时期,第二代从美国获得传播学博士学位、各有专长的学者的加盟,使传播研究在台湾逐渐迈入成熟阶段。但由于研究者大多曾在美国深造,因而其关注领域及研究内容、方法均难脱开美国传播研究的窠臼。这一时期的特征是以行为科学、实证研究为主,但主题多数为测试西方传播理论。自90年代开始台湾传播学研究进入了多元化发展时期。来自欧洲的文化分析、批判学派、诠释学等理论的介入,打破了量化及实证研究独霸天下的局面,内容分析及调查方法在整个研究中所占比例明显降低,符号学分析、框架分析、言说分析等质的分析方法日渐增多,甚至还出现了数学模式、系统设计等方法。总之,世纪之交的台湾传播学已逐渐摆脱过去40年中的单项、美式、实证的导向,进入多元与深化的崭新发展阶段。 在香港,相对严谨和系统化的传播学研究约始于70年代中后期,标志性事件就是美国传播学泰斗施拉姆到香港中文大学短期任教并创办了传播学硕士课程,开展了亚洲新闻的研究。80年代,随着更多在美国学有所成的本土学者回港,研究阵容和成果都明显强化。进入90年代后,来自本土、大陆及海外的学者汇集香港,学科背景、知识框架的不同,关注领域及研究题材的宽泛多元,使得香港传播学逐渐成为中西交汇之地。 历史上,澳门曾经是我国现代报业的发祥地之一⑦,但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则较为滞后,研究队伍、课题都相对较小。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与内地及香港的交流有所加强。如邀请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师赴澳门大学担任客座教授,澳门学者参与在香港举行的“亚洲新闻传播与社会变迁研讨会”等。 90年代以来,两岸三地传播学学术交流日益频繁和深入。香港作为多种文化的交汇点,其传播研究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与港台传播学者的交流,使内地学者了解到最新的研究信息和规范的研究方法;而香港学者关于大陆传媒的研究成果、大陆学者对于港台等地传媒生态的考察等,都在不同层面上加强了两岸三地的情感沟通和学术互动。随着香港、澳门相继回归祖国怀抱,以及和平解放台湾问题呼声的日益高涨,港澳台与大陆的交流必将呈现出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可望成为21世纪的最大显学 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韩非子称儒学说为“显学”(famous school),即著名的学说、学派⑧。历史的发展证实了这一论断,儒学确已成为中国大部分伦理、教育、政治以及宗教的基础。21世纪是“对话的世纪”,以研究人类传播现象为目标的传播学是否会成为这个世纪的最大显学?笔者对此抱有充分的信心。 这一判断首先来自对我们所处时代及未来的基本认识。信息产业是21世纪的先导产业,信息高速公路正在以其后来居上的势头成为“创造21世纪财富的主要渠道”,而信息与传播是分不开的,信息高速公路本身就包含了信息及其传播载体两层意思。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信息社会时代不仅仅是技术的,而且也是不同文化背景人们的关系” ⑨。西方发达国家在进入信息化时代以后,传播学逐渐成为大学文科的主流学科,正是其适应社会和经济发展、应对传播国际化的挑战的举措之一。总之,由于信息高速公路越来越成为生活的主要舞台,才促使传播学有可能成为与各种学科最广泛交叉的学科,这种交叉势必将传播学引向“细化”与“玄化”两个极端——一方面,与传播学相关的各分支学科将获得极大发展;另一方面,又有可能导致传播学走向整合的全息文化研究,即对传播意义的追寻。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学者撰文猜测:“传播学有可能成为未来最大的显学之一,成为博大精深的学问。⑩” 这一判断还来自对传播学在当代中国的理论及实践意义的思考。在与国际接轨、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时,如何发挥传播学对实践界的引导、培训及监督作用,不仅是中国社会发展战略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且已经成为当务之急。通过研究实践来建立自己的假设和理论模型,既推动实践发展,又突出了传播学的中国特色;为大众传播实践界及时提供理论、理念上的教育和培训,形成双向互动的良性循环;站在人文及社会发展的高度,审视并监督在市场化过程中出现的种种价值观偏离及道德水准降低问题,提醒媒介走一条良性发展的道路,避免重蹈西方社会的覆辙。这正在成为传播学者乃至所有知识分子的关注焦点和神圣职责。 鉴于上述现实,在中国已经呈现起飞态势的传播学,21世纪可望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 注释: ①参见丁淦林《我国新闻传播学学术研究的现状》:“1957年初王中教授讲新闻学原理时,曾提及传播学。当年6月以后,再也没有人提起了。”转引自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新闻学》1999年第2期第19页 ②袁军等:《要从扎扎实实的研究做起――访<新民周刊>副主编裘正义》,《传播学在中国――传播学者访谈》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292页 ③见美国著名传播学者、斯坦福大学传播系教授艾文•罗杰斯的评价,转引自袁军等《艰难的起飞――访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陈崇山》见《传播学在中国――传播学者访谈》,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186页 ④同上,第187页 ⑤王怡红《僵化与断裂――对我国研究思路的传播反思》,见《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年第4期第24页 ⑥见“高校经典教材译丛”总序,华夏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 ⑦我国领土上第一份现代报纸(1982年葡文《蜜蜂华报》)和第一家中文现代期刊(1828年中、英文对照<依泾杂说>)的诞生地均为澳门 ⑧见《韩非子•显学》:“世之显学,儒墨也。” ⑨参见国际大众传播研究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1999年11月的会刊报道 ⑩引自朱光烈为第六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提交的论文《未来传播学的两点猜测》 (作者系北京广播学院主任编辑,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
|
回复话题 |
||
 上传/修改头像 上传/修改头像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