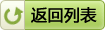|
文学评论参考论文(一)
查看(1754) 回复(0) |
|
 lyh2006 lyh2006
|
发表于 2010-08-18 19:19
楼主
——老舍《断魂枪》的文本分析
刘俐俐《民族文学研究》2006.04 内容提要:以探索《断魂枪》艺术价值成因为目的,首先从结构主义入手,发现三个人和一件事的故事框架聚焦于“传”还是“不传”。其次从原型理论入手,发现沙子龙以“不传!不传!”的态度而使自己成为“最后一个”,“最后一个”作为空白点是文本艺术价值的重要成因,也是老舍“末世人”情绪的艺术选择。 关键词:《断魂枪》最后一个 空白点 末世人 老舍的短篇小说《断魂枪》写于1935年初秋,在老舍毕生写下的短篇小说里,是一篇重要作品。在诸多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中,《断魂枪》是被选人最多的短篇之一。寥寥五千余字的短篇,何以具有如此久远的艺术魅力?本文借助叙事学、结构主义分析方法和原型批评理论分析《断魂枪》艺术价值成因。 一、结构主义分析方法与“不传!不传!”的心理聚焦 《断魂枪》的故事线索非常简单,小说用第三人称叙述出了三个人和一件事。用老舍自己的话说,就是《断魂枪》是自己所要写“二拳师”中的一小块。“在《断魂枪》里,我表现了三个人,一桩事。这三个人与一桩事是我由一大堆材料中选出来的,他们的一切都在我心中想过了许多回,所以他们都能立得住。”结构主义叙事学认为,一个叙事性文学作品,从平衡起步,然后出现不平衡,经过努力再到平衡,这样不断转换所完整的全过程就是一个完整的叙事。这个思路也可以用来分析人物与事件形成的关系:如果我们将沙子龙的心理作为一条平衡线索,将孙姓长者和王三胜的心理作为另一条平衡线索,那么,他们的矛盾纠葛就集结于沙子龙“传”还是“不传”他那套“五虎断魂枪”上。沙子龙打定了主意“不传!”,表示“那条枪和那套枪都跟我人棺材,一齐入棺材!”以此获得心理的平衡。可是,对于王三胜以及孙姓长者来说,心理却大不平衡。小说叙述到,王三胜在土地庙前拉开场子,要“以武会友”,并且以“神枪沙子龙是我师傅”相标榜,引出了颇有几手真功夫的孙老者,王三胜引领孙姓长者来到沙子龙家,希望沙子龙在孙姓长者面前表演一番,孙姓长者的潜台词是希望学习这套枪法。可是却遭到了沙子龙先是搪塞,搪塞不行继而断然拒绝。孙老者无奈地走了,王三胜也从此看不起沙子龙。可以说,王三胜以及孙姓长者的心理是不平衡的。一方不平衡,一方平衡,这就是矛盾,形成了对峙,焦点何在?三个人的故事或者说矛盾就纠结在“传”还是“不传”的问题上。这个故事构架在老舍是具有深刻思索的。老舍自己曾经回忆说:在写作《断魂枪》的这个时期,“事实逼得我不能不把长篇的材料写作短篇了,这是事实,因为索稿的日多,而材料不那么方便了,于是把心中留着的长篇材料拿出来救急。不用说,这么由批发而改为零卖是有点难过。可是及至把十万字的材料写成五千字的一个短篇——像《断魂枪》——难过反倒变成了觉悟。”“觉悟”这个词含义非常丰富而且耐人琢磨。沙子龙的“不传!不传!”是老舍三个人一桩事的“文眼”所在,甚至是老舍自己所说的“我心中想过了许多回”的全部落脚处,深藏老舍艺术匠心,自然具有值得探讨的空间。要探索“不传!不传!”,我们先来考察老舍的叙事艺术和匠心。 二、第三人称的叙述与个人情调的互渗 《断魂枪》是第三人称叙述,但是老舍的高明之处在于它既充分地利用了第三人称观察和出入的便利,又充分调动了叙述语调的功能,还在叙述的同时刻画了沙子龙的形象。可以说老舍将第三人称可能的艺术效应发挥到了最大限度。 1、充分地利用了俯视角的便利叙述出时代的氛围和变迁。在小说开篇,叙述者就叙述出“沙子龙的镖局已改成客栈”。然后用具有历史沧桑感的慨叹语调描绘出时代的变迁:“东方的大梦没法子不醒了。炮声压下去马来与印度野林中的虎啸……江湖上的智慧与黑话,义气与声名,连沙子龙,他的武艺,事业,都梦似的变成昨夜的……”叙述者概括这个时代是“这是镖局已没有饭吃,而国术还没有被革命党与教育家提倡起来的时候”。 2、在叙述中自然地刻画出沙子龙的形象。诚然,叙述者有不少文字叙述了沙子龙形象,沙子龙的形象和经历,在民间的威望,以及眼下沙子龙的处境。艺术直觉告诉我们,沙子龙是小说的主角,但是文本前半部分在实际上却用了较多文字描写了他的徒弟们以及王三胜在土地庙前摆开的练把势的场子以及与孙姓长者的交手等。在这些人对于沙子龙的赞叹、景仰和崇拜的感情中,沙子龙影子似地无时无刻不在读者心中,这个艺术效果是借助于间接描写获得的。金圣叹评《西厢记》时提出了“烘云托月”的写法。意思是以正面描写衬托出更值得描写的对象。《断魂枪》中对沙子龙的描写,准确地说是通过他人对沙子龙的感情、态度间接或侧面描写。老舍通过描写和叙述各色人等对沙子龙的久已敬仰和崇拜衬托沙子龙身份和威望,为沙子龙“不传”的选择先期作铺垫,以便形成较大的落差。沙子龙在读者心理中期待值越高,后面沙子龙拒绝演习“五虎断魂枪”的时候读者心理落差越大,艺术效果越好。 3、叙述中透着苍凉的情调,大势所趋的悲凉时代氛围在情节进展同时顺便得到传达。我们可以追问,这种苍凉情调是属于谁的呢?属于叙述者?还是属于沙子龙,从读者的艺术感觉来说,这份感受和悲凉既可看成是属于沙子龙的,也可看成是属于叙述者的。怎样解释都可以,“今天是火车,快枪,通商与恐怖……”叙述者与沙子龙的感受互相渗透,难以分得清究竟是谁的感慨。无论是谁的感受,皆属悲音。叙述透着苍凉的情调所产生的艺术效应,既衬托人物心理,又赋予故事以意义,并且体现出渗透了情调的语言美。 三、“不传!不传!”而成为“最后一个” 在沙子龙拒绝了孙姓长者“教给我那趟枪”的要求,“王三胜和小顺们都不敢再到土地庙去卖艺,大家谁也不再为沙子龙吹腾……”这样的结局之后,小说结尾有一段极具艺术魅力的描写:“夜静人稀,沙子龙关好了小门,一气把六十四枪刺下来;而后,拄着枪,望着天上的群星,想起当年在野店荒林的威风。叹一口气,用手指慢慢摸着冰滑的枪身,又微微一笑,‘不传!不传!”’沙子龙于是获得了一份心灵的平衡和宁静。按照故事逻辑,如果沙子龙不传这套“五虎断魂枪”,他就成为“最后一个”掌握这套枪法的人。沙子龙为什么把自己变成“最后一个”? 为什么要成为“最后一个”的问题是文本的空白点。“空白点”的概念来自现象学家英加登。也翻译成“不定点”。英加登说:“我把再现客体没有被文本特别确定的方面或成分叫做‘不定点’。文学作品描绘的每一个对象、人物、事件等等,都包含着许多不定点,特别是对人和事物的遭遇的描绘。”英加登进而认为,对于不定点在文学作品客体层次的出现允许两种可能的阅读。第一种是企图使所有的不定点都保持着不确定状态,以便理解作品的特殊结构。第二种是补充确定这些不定点,从而再现客体的具体化。也就是借助于想象,以及读者自己 本文原文的人生经验,“填补”许多不定点。我们现在所从事的阅读,是探求作品的特殊结构,以及这种特殊结构具有怎样的意义,即研究性的阅读。《断魂枪》中“最后一个”成为空白点,还有一些独特之处:“最后一个”是由“不传!不传!”而引出来的,而不是已经被描写出来的。由“不传”而成为“最后一个”是该文本的“文眼”。对于沙子龙“不传”原因的猜想,激发读者各自依据自己理解来填补。这是产生艺术魅力的关键部位。依据英加登的理论,探究艺术价值的前审美认识,对于“空白点”不予填补。 下面我们根据平时阅读和经验,描述几种从审美经验中可能产生的填补方式。以便展现艺术价值是如何形成的。 第一,中国民间历来对于家传绝技、秘方等的处理态度是传男不传女,传给儿媳妇,不传给女儿……这与中国以血缘宗法纽带为特色、农业家庭小生产为基础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结构长期稳定、缺少变动有关。血缘基础是中国传统思想在根基方面的本源,实用理性便是中国传统思想在自身性格上所具有的特色。重经验重实际的倾向和思维方式,在自家秘方和家传技艺方面就必然采用保守不传的策略。所以,读到老舍的《断魂枪》,认为沙子龙的不传,缘于为了生活而独占生存技能,这是一般读者最常见的填补方式。我们提出的质疑是,小说开篇不久就有:“沙子龙的镖局已改成客栈”。这套五虎断魂枪已经不能挣钱了,既然如此,沙子龙为什么要当“最后一个”? 第二,沙子龙珍爱自己这套“五虎断魂枪”,虽然现在洋枪洋炮已经惊醒了古老东方的大梦,古老的武术已经毫无招架之力,但是,沙子龙依然将“五虎断魂枪”视为艺术,并且执意将这门艺术珍爱地保存,和自己一道进入坟墓。千万不能在他人手中被糟蹋了。这个解释是建立在沙子龙热爱、珍视传统文化的形象把握基础上的。与第一种填补方式相比,显然对于沙子龙的精神境界评价要高得多。 第三,沙子龙的形象是我们民族民间具有非凡智慧和极高境界的代表。应该有更深刻的理解。这个看法来自我国老舍研究专家关纪新的研究(我将文学史研究专家和作家论式的研究专家对于作品的理解,界定为特殊的填补,因为他们在自己的研究著作中对于“空白点”是要填补的,评说不就是填补吗?)。关纪新在《老舍评传》中对于《断魂枪》的评述是:“而‘断魂枪’法的主人沙子龙,一点也看不出他哪怕起码是在心劲儿上的抗争,他好像早就心宽气宏地接纳了那命运的陡变,作家构思与运笔的精妙之处,也许恰恰在此处,从沙子龙口中连连喊出的‘不传’,明示着读者,他业已参透一切并重新拿定了方寸,绝不去跟迎面压过来的时势较真用气,绝不发泄任何心中不悦,这可就不是常人所能修养到的境界了:当我们捕捉到了这条思路,再把寻觅的眼光略微放远一点儿,便可以恍然想到,我们的古老民族确曾有着为数不多的文化人,他们面临眼前文化百相的风云翻覆,胸中虽郁结过层层叠叠的文化块垒,并在偌长的时间里孜孜求索,但是,他们毕竟依赖于个人的悟性,艰难地跨越了某道心理极限,逐渐获取了一双冷眼,一份静心,进而试图借用一副历史老人的心肠,来领略和透视大千文化的嬗替锐变。沙子龙,可能就是作家比照着这种心态,塑造出来的一位甘为旧有美质文化而殉道的末路英豪,他决计要刚毅地迎纳现实的轰击和毁灭,走上与心中的完美事物(虽然是历史性的)共相厮守的终极之路,而把不尽的哀伤、悲凉,悉数留给未达到相应顿悟的芸芸世人。”关纪新教授的填补方式,与前面一种有相似之处,就是“走上与心中的完美事物(虽然是历史性的)共相厮守的终极之路”,但是就其原因的解释,还是有差别的,显然关纪新教授对于沙子龙的精神境界的评价要更高。 由于研究者将自己的研究成果诉诸于文字,所以我们在老舍研究领域还可以检索出一些对于沙子龙“不传!”原因的理解,姑且都可视为各种填补。仅就以上所列,可以证明,“最后一个”是一个空白点,也是这个文本艺术魅力形成的重要机制。下面我们进而从原型批评的角度来分析“最后一个”。 四、“最后一个”与原型批评 “最后一个”是一种故事讲述的模式,也可以理解为是一个“原型”。回顾中外文学我们发现,许多优秀作家都喜欢讲“最后一个”的故事。有的在字里行间透露出“最后一个”,有的直接以之命题……形式不一。比如,白先勇的《金大班的最后一夜》、《永远的伊雪艳》,法国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课》,汪曾祺的《鉴赏家》(描写最后一个鉴赏家),李杭育的《最后一个渔佬》,肖克凡的《最后一座工厂》(描写国有企业改革中传统工厂运行方式的终结),聂鑫森的《棋殇》(在抗日战争背景中,描写围棋大师江泽洋不屈的民族气节和个人操守,江泽洋是最后一个有气节的围棋大师),姜安的《远去的骑士》(描写骑兵兵种消失过程中的“最后一个骑兵”的心理生活),李杭育的《最后一个渔佬》。 为什么“最后一个”如此得到作家们的青睐?在我看来,符合小说的本性是首要原因。小说在本质上都是回忆性的。所叙在逻辑上皆属于过去时态的事情,而“最后一个”是一个人、或者一件事、或者一种生活生产方式的完结,也是属于过去时的,且由于是最后一个,自由总结、抒发感慨和寄托情思都变得更加自由,与小说回忆状态下的叙述本质恰好相互吻合。第二个原因是,“最后一个”与人类本性中喜欢哀挽和悲伤情调有关。而文学就是利用了人类这个天性来造艺的。钱钟书在《管锥编》的第三册“全汉文卷四二"列举和比较了中西方文学和艺术中的多则材料来说明“最谐美之音乐必有忧郁与偕”的道理,用雪莱原文的表述就是“the melancholy which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sweetest melody”。前面我们所列举的那些“最后一个”的小说作品可以为证。 以揭示和探究作品艺术价值为目的的文本分析,可以将“最后一个”作为批评切入点。原型理论家弗莱在《批评的剖析》中提出,文学作品这个“假设性的语辞结构”(hypothetical verbal structure)中具有一种叫做“文学性”的东西。弗莱说:“无论在哪里只要我们遇见这样的语辞结构,我们就遇见了文学。”那么,文学性是怎样产生的?弗莱认为,对于神话不同程度的移用,是文学性生成的来源。一切文学叙述其实都是在神话和自然主义这两个极端之间展开的。弗莱所说的神话,就是原型,弗莱意义上的原型有两个主要来源:希腊神话和《圣经》。弗莱所说的“移”,其含义是对于原始神话原型的改变和创新,弗莱所说的“用”,其含义是对于原始神话原型的继承和沿用。有“移”,才有新鲜感,传达新的感受和体验,有“用”,才能保证与其他原型的关联,才能被作为原型来理解。弗莱还认为,在一个平常的和外部客观世界的逻辑、情理都很一致的故事里加进一些神话的“移用”因素,故意使“故事”脱离和生活的外部类比,显得这样的事情只能发生在故事里,于是这个故事因怪诞的情节而获得了一个抽象的文学性质。“抽象的文学性质”的意思,就是在不同民族文化之间可以取得同情的共同感以及生成的意义等。弗莱的原型批评理论的本质是文化研究,必须在文化河床中来把握原型。这给予了文学批评开阔的空间。 可以从宽泛意义的原型来理解“最后一个”。考察具体文本中“最后一个”的“移用”的情形,是抵达作品艺术价值构成的途径。同时,作为原型来理解“最后一个”,可以通向对于作家的考察以便进入文本间性的研究。让我们带着以上思考,依然回到老舍和他的《断魂枪》的讨论。 老舍曾经表达过末世人的情绪。他在《诗二首?昔年》中有“我昔生忧患,愁长记忆新;童年习冻饿,壮年饱酸辛。滚滚横流水,茫茫末世人”的诗句。虽然这首诗写于新中国,但是作为追忆,他证实了自己曾经有过的“末世人”情绪。“末世人”可以理解为是特定时代具体的人,也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心理感受,也可以理解为是含有丰富意蕴的比喻……在我看来,末世人的心态是很普遍的,凡是身处末世,产生了没落感受的人都可以被认作是末世人。但是老舍却在末世人的基础上写出了更具有特性的、最值得玩味的“最后一个”。事实是,大凡写“最后一个”的作家,都会有末世人的情怀,或者挽歌情怀,也就是说,“最后一个”作为原型批评方式,可以和对于作家的考察联系起来,比如所述我国当代重要的短篇小说作家聂鑫森的小说《棋殇》。聂鑫森还有《笔殇》等小说作品,都是写文人的人文操守的。聂鑫森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古典主义情怀浓郁的人。他自己说过:自己写作的资源根基是湘潭这座古城。他说:“我生于斯,长于斯,自小就浸淫在古城一种厚重的文化和历史的氛围中,不可自拔。而街头巷尾,俯拾皆是的传说、歌谣,更给了我最早也是最为强烈的文学熏染。这使我在未来走上文学创作之路后,得到了一种选取题材的便利,并往往流露出一种历史的沧桑感,凸现出一种自我陶醉的‘古典情怀’。” 再进而从文本之间的关系即互文性来理解“最后一个”。美国小说理论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家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论述老舍的时候首先将老舍与茅盾相互比较地论述。在夏志清看来,老舍代表北方和个人主义,个性直截了当,富幽默感;他的主人公几乎全部是男人,他总是尽量地避免浪漫的题材。老舍对于个人命运比社会力量更要关心。夏志清认为,《骆驼祥子》是一本深含个人情感的小说,在骆驼祥子身上,老舍表现出惊人的道德眼光和心理深度。老舍显然已经认定,在一个病态的社会里,个人用自己的力量试图求得发展,只能加速自己的毁灭。必须依靠集体行动,这个思想是依托着小说中那个发言人也就是一个老车夫的口说出来的。这个老车夫两次在祥子的生活里出现,每次都使祥子作了一种选择,减少了特有的自尊和自信。或者说,从《骆驼祥子》开始,老舍已经开始非难带有自由主义味道的个人主义。 《断魂枪》写于1935年,《骆驼祥子》写于1937年。两部作品篇幅不同,时间接近,还是可以互相参照的。如果我们认可夏志清对于《骆驼祥子》的分析,我们也可以思考,依据老舍在《骆驼祥子》中的道德眼光和心理深度,也可以推想,在《断魂枪》中,老舍在沙子龙身上,也于末世人心态中渗透有“最后一个”的道德思考和心理深度:即沙子龙已经是一个觉悟者,他觉悟到凭借着那套在民间极有声誉的“五虎断魂枪”,除了能给个人以自尊和名誉以外,对国家和民族的每况愈下没有任何助益。他是个清醒的人。清醒的人才能让自己成为“最后一个”,可以认为《断魂枪》沙子龙对自己所说的“不传!不传!”寓意着“最后一个”,这该不会有错的。 “最后一个”的原型是否必须在作品标题或者字里行间透露出来呢?这是艺术理解的问题,也是艺术技巧处理的方式问题。老舍在《断魂枪》中没有“最后一个”的字眼,这种现象在其他一些优秀作家那里也出现过。比如聂鑫森的小说《棋殇》,汪曾祺的小说《鉴赏家》等都没有“最后一个”的字眼。这是中国文学特有的含蓄使然。叙述语言本身的含蓄、细腻等特点,已经可以非常徐缓地将“最后的”的氛围表达出来。 (论文接受“南开大学亚洲研究中心”资助。) |
|
回复话题 |
||
 上传/修改头像 上传/修改头像 |
|
|
|